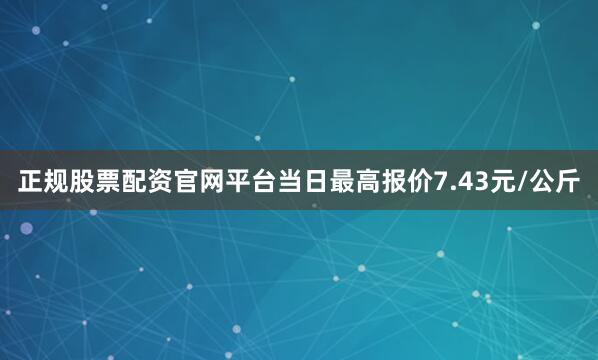一句成谶,令人不胜唏嘘。那篇关于耀邦同志的文字,仅在网络上留下了一天的痕迹,便无声无息地“遁去”。
您可于“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爱思想网”等在线平台查阅本资讯的详尽内容。需提及的是,在整理过程中,我们对某些直白表述进行了删减。尽管如此,该内容最终仍被撤下,原因在于“用户举报后平台审核,内容疑涉违法法律法规及政策”。这一现象颇为引人深思,为何涉嫌违规的内容在其他网络平台上却能顺利发布?
何人高见引发异议,众说纷纭自是常景。或许,我们可以就此展开一番探讨,亦或是各自保持己见,亦无不可。
昨天发的杜高忆:反右亲历记(一)历经波折,经过反复的修订与精简,文章终于得以顺利通过。事实上,这篇文章的灵感源自一本科普著作——《又见昨天》,该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4年3月出版,杜高先生根据其亲身经历撰写而成。在出版之前,该书已经历了一系列严格的审稿流程。
若友人持有不同意见,恳请我们增进沟通,降低抱怨之声。须知,这片园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交流的渠道,更构筑了分享与研讨的宝贵平台,这无疑是件好事。
四处飘零,真挚友情难得寻觅。特此提供以下备用联络方式,愿有缘之人勿让良机从指缝中溜走。
风云变幻,福祸无常。
备胎多保,关注好友。

作者:陶斯亮
随着岁月的流转,历史的长河里,无数璀璨的瞬间被镌刻在记忆之中。今天,我们的目光聚焦于那些在时间的磨砺下愈发闪耀夺目的篇章。
《中华儿女》2008.4
一
在我心底,除了双亲,最亲近的亲人非那位宛如兄长般存在的干爸王鹤寿莫属。
这幅影像深藏于我的影集之中,定格了我与父亲陶铸及干爹王鹤寿在延安那段难忘的时光。我那时的年纪尚幼,四岁稚龄,紧靠在干爹温暖的怀抱里,却忍不住好奇地回过头,望向父亲。两位父亲面露欢愉,他们的笑容灿烂而真挚,而我则天真地抓着头发,脸上交织着童真与好奇,仿佛在问:他们为何如此欢欣?这一刻,生动描绘了我与这两位父亲之间那份深厚的情感联系。

1945年,在延安这座古城之中,陶斯亮与其干爹王鹤寿以及父亲陶铸(站立于右侧)共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我的父亲与他的干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南京军人监狱里,曾是并肩而战的难友。他们都是那所监狱中最为英勇、坚韧、刚强的共产党员,彼此间的敬意与钦佩之情如泉水般涌现,由此结下了牢不可破的生死之交。在党的援救之下,他们一同重获自由,随后先后抵达了延安,他们的友谊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传闻中,他们与胡耀邦先生并称“延安桃园三结义”,成为了流传一时的佳话。
尽管年纪尚轻,我已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而这位干爸,便是我自己挑选的。在摇篮之中,面对众多前来探望的父亲好友,我总是显得冷漠,唯有干爸的到来,能让我不由自主地感到喜悦,渴望他的怀抱,对他报以欢快的笑声。然而,当他离去,我便会无法自制地放声大哭,那份悲伤的情绪会持续良久。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时至今日仍难以寻得合理的解释,或许只能将其归因于“缘分”二字。
事实为证,自我年方一岁之时,便选定了我的干爹,其智慧堪称卓越。在我人生旅程中,尤其是童年及少年阶段,他给予我的父爱,其深厚程度与我的亲生父亲相较,毫不逊色。
我至今对在哈尔滨干爸家中度过的温馨时光倍加珍惜。回想起童年,我可能确实是个被过度宠溺的小公主。随着年龄的增长,干爸最常讲的一个笑话是:“亮亮,你还记得在哈尔滨时,你一个人就能吃掉半只鸡的趣闻吗?”
我自然是记得,那时的我任性之极,竟至不允许干爸与干妈举筷一用。
在东北解放战争的烽火年代,我的父母亲均英勇投身于战场的最前线。幸得干爸的无微不至的关照,我在那炮火连天、白雪皑皑的岁月中,得以在东北的崇山峻岭之中,平安度过了我的童年时光。
二
在全国迎来解放的曙光之际,我随父母踏上了南迁的旅程。面对广东独特的语言环境,以及对于干爸的深切思念,父母无奈之下只得将我送往时任冶金部部长的那位干爸家中。在那儿,我度过了四年的童年时光。干爸对我关怀备至,我的日常起居无不沐浴在他的细心照料之中,他的宠爱更是成为亲友间传颂的佳话。

王鹤寿任部长。
“亮亮!亮亮!”我的声音中充满了兴奋,我欢快地冲出门去,迎接他的到来。啊,那段时光,真是难以忘怀。
往昔,学生们惯于自备午餐,于破晓时分将一只铝制饭盒悄悄藏匿于书包的隐蔽处。待抵达学校,便将饭盒放入蒸笼中加热。考虑到干爸每日都会亲自检查我的饭盒,厨师便总是慷慨地将各种美味佳肴满满当当填入其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学们渐渐了解到我的饭盒里总藏着诱人佳肴。一到饭点,女同学们便会好奇地围过来:“亮亮,你饭盒里的是什么美味呀?”话音刚落,她们便争相品尝,而我却只能空手离开。
我终究下定决心,取回饭盒后,双手紧握,毅然决然地未敢轻启盖子。直至她们各自享用完自己的餐点,我方才缓缓打开盖子,开始品尝干爸爸为我精心烹制的美食。
数十载光阴荏苒,每当我们与昔日初中时期的同窗好友重温往昔,总会不禁哑然失笑。在那个年代,饮食对于人们而言,无疑是生活中的一件头等大事。
在这四年北京的时光里,我不仅沉浸在干爸干妈无微不至的关爱之中,更在诸多方面受到了干爸的深远影响,可以说,他正在塑造着我的品格。他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对党的事业的满腔热忱与虔诚,对原则问题的不屈不挠,他那固执却又率真的性格,以及他那外表刚毅严肃、内心细腻体贴的情感特质……这一切,都对我人生观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王鹤寿致陈云夫人信手迹
难忘小事:
在北京的高中岁月里,一日,我正在家中笔耕不辍,撰写入团申请书。团支书忽然点拨我,需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发源地进行深入挖掘。对此,我茫然无知,既不清楚“小资产阶级”究竟为何,更对“思想根源”这一概念感到困惑。
我那干爹见我抓耳挠腮,好奇地问清原因后,忍不住批评道:“胡说!你这小不点儿,哪来的小资产阶级观念?不过是太放纵自己了而已!”
霎时顿悟,我自封为“自由散漫”的代表,果然成效显著,不久便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团组织。
甚至,我的日常起居与饮食习惯也深受干爸的影响。例如,尽管我不太偏爱鱼类的味道,却对那弹牙多汁的酱猪蹄情有独钟,对荞麦面也尤为喜爱,更对侯宝林先生的相声艺术陶醉不已。
在阅读领域,我自认为还算得上热忱,但与我的干爸相比,差距却是显而易见的。在共产党的干部队伍里,鲜有人能像他那样,夜以继日地投身于书海之中。他的周围,总是堆满了厚重的已阅书籍,以及另一堆待阅的佳作。

王鹤寿、王昆
三
在那个充满回忆的八十年代,我有幸在干爸的家中度过了一整年。那座位于麻线胡同的四合院,因其古朴与雅致,更因干爸这位手不释卷的长者,增添了几分书卷的韵味,让我时常感觉自己仿佛漫步在书香四溢的书院之中。
在1981年前后,我的干父提议,让我一同前往北京饭店会晤一位拥有美国国籍的华裔友人。据我所知,中纪委的职能似乎与外籍人士并无直接关系。那么,这位华裔友人有什么特别之处,以至于需要中纪委领导亲自前去看望?我对此充满好奇。
干爸曾言,那位来自美国的女士,曾与关向应同志结为连理,亦曾是他在1926年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时的同窗。二人还曾一同出席过党的六大。归国后,干爸与该女士先后身陷囹圄。女士不久后背弃了革命理想,出狱后与一名男叛徒一同投靠了国民党,并在解放前夕逃往台湾。1964年,夫妇俩移居美国,投身商界,生意兴隆,生活富足。此次回国观光,女士多次向相关部门提出申请,渴望能与在莫斯科时的旧友重逢。组织上便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愿独自面对这位历史背景复杂的人物,于是便邀请了我一同前往。

关向应、秦曼云在莫斯科
那是一次让我终身难以忘怀的聚会。房门缓缓敞开,映入眼帘的是一位气度非凡的阔绰夫人。即便年过古稀,她依旧保持着精致的妆容,身着鲜艳的绸缎裙衫,下配绿色的喇叭裤,脚踩尖头高跟鞋,颈间挂着项链,耳畔点缀着耳环。老太太首先关切地询问起昔日东方大学同窗们的近况。干爸的回答虽简短,却以平静的语调,令人动容。那些曾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的东大共产党人,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每一位都是英勇无畏的烈士;依然健在的,也都是杰出的人才。
这位老妇人身姿略显不自在,面带愧色。她结结巴巴地向中共中纪委副书记述说了自己1927年遭捕的往事,力图为自己的变节之举寻找理由。尽管如此,她的言辞中仍流露出一丝真诚的关切,她细致地询问了关向应同志英勇牺牲的细节。她还表达了自己愿意为祖国统一的大业全力以赴,决心为共产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的决心。

秦曼云和盛忠亮
最后,她满怀同情地问道:“这些年来,你承受了多大的痛苦呢?”
干爸始终以一种镇定自若的姿态存在,悠然地倚坐在沙发上,手中执一把折扇,轻缓地摇动。听闻此言,他淡然一笑,轻描淡写地说道:“这不过是党内寻常事务,并无特别之处。”
一句话,老太太无言以对。
凝视着这对携手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耄耋夫妇,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位干爸,身着朴素的旧衣,脚踩布鞋,一头白发随风飘扬,面容坚毅,一眼便能洞察他经历的沧桑岁月。在解放前,他六次身陷囹圄,却始终坚守着一名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信念。

秦曼云(左二)
在回家的路上,我特意向干爹请教:“你看,那些虽然背离了革命道路却过上了富足生活的,到最后还是受到尊敬。而你,历经国民党六次牢狱之苦,共产党十年的劳动改造,难道你不觉得有什么遗憾吗?”
“何需懊悔?我选择的道路,完全是出自本意,无人强加,哪有后悔之意?”他语气坚决地答道。
“有人说你们很傻。”
“我愿意心甘情愿地承受,哪怕成为革命中的愚者。”他语气平静地陈述。
闻言,心中油然而生一股崇高的敬意,方才深刻领悟到了“崇高”二字的真谛所在。

黄克诚、陈云、王鹤寿
四
那日,1998年6月21日,犹如一把锋利的刀刺痛了心扉,母亲离我远行,痛楚之情几乎将我淹没,令我难以承受。
1999年3月2日,干爸在九旬之龄离世,踏上了归途。拂晓时分,我匆匆赶至北京医院,映入眼帘的是我最深爱的亲人,安详地躺在白绫的覆盖下。我紧紧地将他拥入怀中,内心悲痛至极,却泪流不出。一位智者曾教导我,在亲人逝去的时刻,切莫放声痛哭,而应保持庄严与肃穆,用虔诚的心灵为逝者的灵魂送行,愿其灵魂得以升入天堂。
在送别的仪式上,七十余位亲属的身影汇聚一堂,宛如一片笼罩的乌云。他们之中,既有老王家,也有谷牧家、王蒙家,乃至我家——即陶铸的家。这些来自不同家族的长者、青年和儿童,今日皆化身为干爸的亲人,他们怀着深沉的哀痛与崇敬,共同为他送上一程。
王颖阿姨,身为家中的干爸夫人,稳居最显眼的位置;紧接着,便是干爸的亲妹妹林浦女士;紧随其后,则是王昆。王鹤寿侄女,歌唱家。在我紧随大姐与周巍峙姐夫之后,紧接着便是我的位置,而在我之后,敬敬与微微也各占一席。显而易见,这样的座次安排,无疑是将我视为家中的重要一员。
我的忽然加入亲友聚会,让不少人大感意外,面露惊奇。胡锦涛同志亦如此,他逐个与我握手,经过我时,又不由自主地回头望了一眼,眼神中透露出一抹困惑,仿佛在内心深处疑惑:你为何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不日之后,电话铃声响起,是他亲自拨来的。我向他倾诉了半个世纪以来与干爸之间深厚的父女情谊,并告诉他我计划撰写一篇关于干爸的纪念文章。胡锦涛幽默地打趣道:“你几乎成了撰写纪念文章的专家了!”

“昔日领导,往昔挚友,您为何不等我片刻,便急忙踏上了归途?”这番话中饱含着难以言表的感伤,读之令人心生惋惜。
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我见证了众多人热泪盈眶,尤其是他的资深秘书和贴身工作人员,他们的哀伤尤为深切。王颖阿姨更是悲痛难当,几近无法自持,不得不依靠旁人的扶持。
令我倍感惊讶的,乃是被尊称为“铁面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在干爸的灵柩之前,他默默伫立良久,眼角泛起淡淡的红晕,泪珠在眼眶中微微闪烁……
去年新春伊始,我有幸与朱镕基总理就此事进行了交流。他回忆起在东北工业部任职的时光,提及鹤寿同志曾是他麾下的得力部属,“我对鹤寿同志怀有无比的敬意!”身为国家总理的朱镕基,能够因为半个世纪前的老领导而动容落泪,这无疑彰显了他们之间非凡的人格魅力。
八载光阴似箭,我竟然迟迟未曾提笔,写下关于干爸的篇章。今日,正值与干爸永别之际,我静坐桌前,沉心落墨,心中涌动着与干爸终身的父女情深。未曾料到,我对他的怀念并未随岁月消减,反而日益浓烈。干爸那般真诚、纯洁、坦率的品格,在世间实属难得,对我而言,他已成为一种精神图腾。在这物质至上的时代,父母的在天之灵,以及干爸的灵魂,将指引我不迷失自我,让我沉浸在坚守信仰带来的那份充实与幸福之中。
2024配资查询网站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公司配资他们确实没翻出如此生草的译名
- 下一篇: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