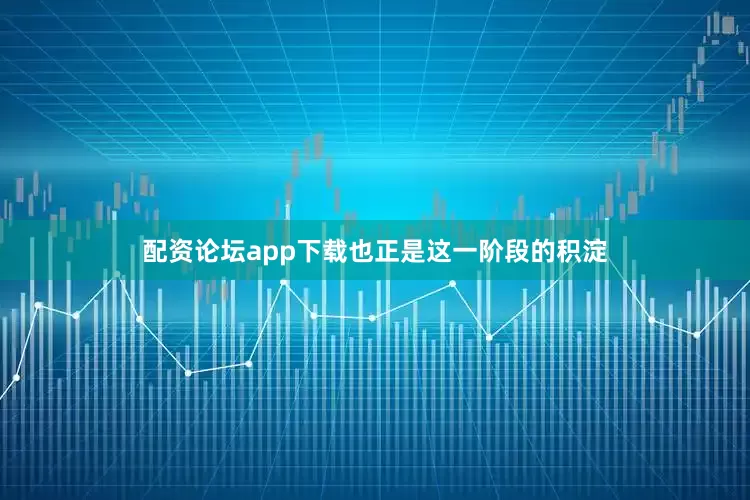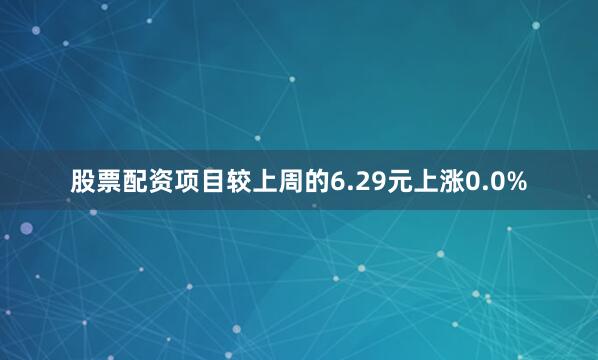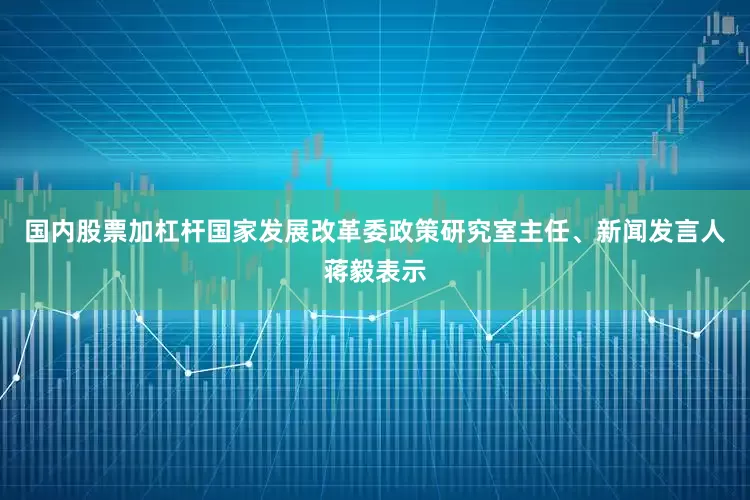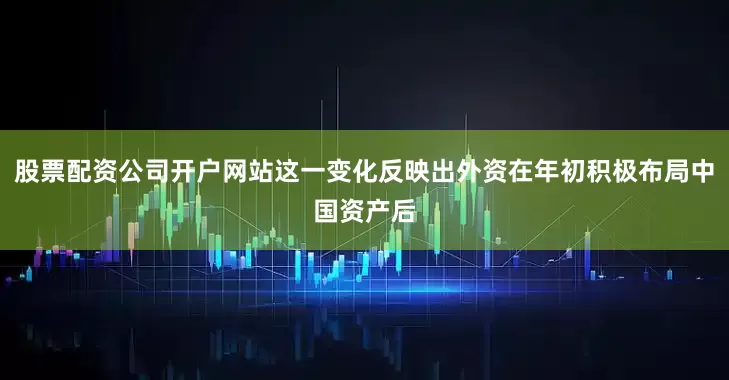摘自:中国新闻网(发表于2008年9月23日)
[附纪录片]
梁漱溟,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杰出人物,亦是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应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邀,他踏足北京,跻身全国政协委员之列。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遭遇了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自此,他由毛泽东的座上宾沦为了“反面教材”,这也标志着他与毛泽东之间长达数十年的交往几乎走到了尽头。
这起事件的全过程,于1953年9月8日至18日,分别在召开的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展开。全国政协委员梁漱溟受邀出席了这两次会议。
9月8日,国务院总理并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出席了提前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并就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表了重要讲话。
9日上午,各小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小组召集人章伯钧的发言完毕,梁漱溟先生随即对《人民日报》新设的读者来信栏目发表了个人感言。
此举既彰显了人民对公共事务的深切关怀,亦体现了党和政府能够及时倾听民意、解决问题的决心。此种精神,在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中,理应得到持续传承与弘扬。唯有始终秉持民主原则,党领导层能够广纳众言,方能将建国事业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参与,进而极大地提升其成效。
9日下午,会议临近尾声,周总理鉴于讨论未尽兴,宣布次日将由个人继续发表大会演讲。在告别会场之际,周恩来向梁漱溟提议:“梁先生,请您明日也发表一下您的见解,如何?”梁漱溟毫不犹豫地应允:“当然可以,我明天将在大会上发言。”

年轻时的梁漱溟
返抵家中,梁漱溟心中所想,既已受命于党的领导核心,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自当贡献有益之词以裨益领导党。基于此念,他严谨地着手进行了充分的准备。
10日的会议发言异常积极,梁漱溟未能如愿上台。在会议间歇期间,他向周恩来总理递上一张便条,提及北京代表发言的机会较多,恳请总理优先考虑外地代表的发言机会,并表示自己准备的口头发言可以转为书面材料提交。周恩来总理回复他,无需过多担忧时间安排,会议的日程可以适当延长,他将在次日的大会上获得发言的机会。
在11日的午后集会上,梁漱溟发表了演讲。正是这场演讲,引发了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之端。
鉴于回眸之需,加之论述之必要,不妨对梁漱溟的言论进行一番较为详尽的摘录。
梁漱溟说:
“连续数日聆听报告,我们得知国家已步入计划建设的崭新阶段,众人的心中无不充满了激动与期待。我也想借此机会,从我的政协成员身份以及过往的经历出发,发表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昔日的梦想,是见证一场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伟大建国运动。四十年前,我曾投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中,那时我只知追求政治的变革,而对如何规划国家建设一无所知。然而,几十年来,我始终怀揣着规划建国的愿景,尽管当时并不了解新民主主义的理念,但我的理想与目标与之大致契合。
鉴于国家建设的蓝图需在各个层面实现协调与统一,我推测政府除已向我们阐述的建设重工业及改造私营工商业两大领域外,对于轻工业、交通运输等领域的相应发展,亦应有所规划,并希望将这些计划告知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
鉴于建国运动需广泛动员和依靠群众以实现既定目标,这让我不禁深思群众工作的关键性。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我以为工会组织足以作为依托;而在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方面,店员工会、工商联以及民主建国会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至于农业的发展,我想或许还需农会的助力。尽管农会在土地改革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在土改之后,其影响力似乎有所减弱。因此,目前似乎唯有乡村的党政干部能够成为依靠。然而,据我所知,乡村干部的作风往往带有强迫命令和包办代替的倾向,无论是素质还是数量,似乎都存在不足。按照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群众,尤其需要加大教育投入,仅仅传达政令是远远不够的。我期望政府能够对此给予更多关注,并作出更为妥善的安排。此为第二点。
更有其三,这是我想着重阐述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者说乡村问题。在中国近三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中共始终依赖农民力量,以乡村为稳固的根据地。然而,随着城市工作的重心逐渐转移,从农村走出的干部纷纷涌入城市,导致乡村地区变得相对空疏。尤其是近些年,城市工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升,而农村农民的生活却依然困苦,因此,各地乡村的人们纷纷涌向城市(包括北京),城市容纳不下,又不得不将他们驱赶回去,从而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人形容,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同九天之上,而农民的生活则仿佛九地之下,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九天九地”之差,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建国运动忽略了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农民,那无疑是极不适宜的。尤其是中共作为领导党,其过去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农民的支持。如今若忽视他们,外界可能会说我们进城后,对农民产生了嫌弃。希望政府能够对此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梁漱溟发言完毕,现场竟无一人提出异议,反有数人公开表示其观点值得肯定。

梁漱溟与张澜、史良等友
“竟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数十年来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的了解还不够。真是笑话!我们当前政权的根基,工人与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统一的,这一基础不容分割、不容破坏!”
毛泽东的这一表述虽未明言梁漱溟的名字,然而,智者一瞥便能洞察其意,所指分明是梁漱溟。此言遂引起了梁漱溟的特别关注。
此刻的梁漱溟内心充满惊异与不忿。他自问,自己何曾抵制过总路线?他坚信自己对总路线的拥护是真诚无二的。他并非意在削弱工农联盟,恰恰相反,他期望看到工农联盟的根基愈发稳固。于是,他急于辩白,亟需澄清误解。他在会议期间致信毛泽东,但信尚未写毕,会议便草草结束。
踏入家门,他仍旧埋头于书写这封信件。信中旨在澄清,他发言之际,绝无任何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之意图,其初衷不过是为政府福祉着想。他恳请主席能在大会上撤销相关言论,以消除对他个人所持有的误解。

1938年伊始,毛主席于延安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梁漱溟先生。
9月13日,梁漱溟于会场中向毛泽东当面递交了其亲笔信件。毛泽东遂约定当夜进行交谈。然而,因事出突然,当夜谈话并未能深入,误会亦未得到消解。梁漱溟感到极度失望,遂决意不放弃,意图在大会之上再度阐述己见,以期与会者能够进行公正评议。
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逐一重申了9月9日及11日的发言要点,郑重声明自己未曾对总路线持反对立场。然而,当日依旧无人对他提出批评。
“纵然你未曾挥刀杀人,却以笔为刃,伤人于无形。”“众口皆言你是仁人,我却谓你是伪善之徒!”“即便下一届政协有意推荐你参与,亦是因你擅长误导他人,使一些人陷入你的迷惑之中。”“倘若你公开反对总路线,主张重农抑商,尽管你的观点或许模糊,但出于善意,尚可原谅;而你却暗中反对,实则心怀恶意,实属不可恕。”
这位中央领导的结论让梁漱溟心情烦闷,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因言辞失当而引发的误解已根深蒂固。在刚毅个性的驱使下,他置一切于不顾,坚决要求立即发言以澄清事实。
9月18日大会上,梁漱溟发言。
“昨天会上中共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中共领导人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这就因此增加了我交代历史的任务,而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就需要给我比较充裕的时间……”
“我此刻的唯一请求,便是给予我充分的时间表达观点。昨日会议中,各位对我的批评不绝于耳,今日若不让我充分发言,实乃不公。我衷心希望领导党和在座的党外同仁能对我进行考验和考察,赋予我一次机会。同时,我也坦率地表达,希望对领导党进行一番考验。此刻,我询问毛主席,是否具备聆听我详细阐述事情始末的雅量,待我讲明真相后,若您能说梁漱溟并无恶意,这便是我所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泽东曾言,你所求之雅量,我恐怕难以具备。
梁漱溟紧接着表示,主席若具备这份胸襟,我自当更加敬佩;倘若您并不具备这样的雅量,我将不得不失去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回应道:“然则,我怀揣一份雅量,允许你继续担任政协委员。此举,旨在让你成为一活生生的教材,供后人借鉴。”
此刻,梁漱溟难掩心中激愤,言辞决断,是否担任政协委员,实属次要之选。
毛泽东怒斥道:“至于你所说的那事,那是另一码事了。”
梁漱溟续言,共产党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今日我便试着检验一番,这批评与自我批评究竟是虚是实。
毛泽东曾言,于你之身,唯有自我反省或接受他人之评。
会场上发生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与毛泽东顶撞的局面。忽然台下有人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子,梁漱溟滚下台来!
此刻,毛泽东语气温和地提出:“梁先生,今日就请简明扼要,能否控制在十分钟内阐述要点?”
梁漱溟言:“诸多事实待述,十分钟岂能尽言?恳请主席赐予我公正的对待。”
会场上再次响起喧哗之声,众多与会者对梁漱溟的举止表示强烈不满,纷纷呼吁他离场。毛泽东接着说道:
“若剥夺他充分表达的机会,他便会认为这不公正。然而,一旦给予他充足的时间,他或许会滔滔不绝数小时,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并非短短数小时、几天甚至几个月就能厘清的。需要明确的是,梁漱溟所面临的问题并非仅属于他个人,而是借此机会揭露其反动观点,帮助大家明辨是非。对梁漱溟的反动倾向,若不彻底揭露,不进行严肃的批判,都是不够的。在此,我再次建议,能否再给他十分钟,让他简洁地陈述一下?梁先生,您看如何?”
梁漱溟依旧以“十分钟不足以展现我的观点,请给予我公正的待遇”的回应。
毛泽东最后言道:“梁先生,我并未限制你长篇发言,你指责我缺乏‘雅量’,然而众人亦未限制你发言,难道众人皆无‘雅量’?你抱怨未能得到充分发言时间是不公,但众人亦不赞同你发言,那么何为公平?你意下如何?”
梁漱溟不悦道:“主席定夺。”
此时,提议将此问题提交表决,以视支持梁漱溟继续发言者与反对者之众。毛泽东率先举手支持梁漱溟,其他中共领导人亦纷纷响应。然而,与会的大多数人却表示了反对。梁漱溟无奈之下,只得离席,这场持续已久的僵局方才得以告终。

梁漱溟
此事不久后,梁漱溟便向全国政协提出申请,决定暂时退出各类会议及活动,以便能够投入更多精力于阅读学习,闭门反思。
在深刻反省之际,梁漱溟意识到自己犯下了严重错误,不应如此无礼地冒犯毛主席这位伟大的领袖。在众多亲友和家人的劝慰与支持下,梁漱溟于9月22日伏案进行自我检讨。
我反思自身思想错误的根源,显然是源于阶级立场的偏差。在解放前,我对阶级立场的观念持怀疑态度,这种心态持续已久。自从共产党运用阶级理论建立新中国后,面对现实,我有所觉悟,也曾怀着自责的心情试图摆脱旧有的立场,转而接受无产阶级的立场。然而,实际上我仅仅是心有所动,并未真正跳出旧有的思维框架。
譬如,我亲眼目睹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与敬爱,而相较之下,我自感差距甚远。这其中的原因,便在于我未能彻底摆脱旧有的立场,无法在心理上与他们融为一体,共同凝结。
譬如,在诸多场合,常目睹众多人士对共产党与毛主席赞誉有加,而自己则仅限于鼓掌附和,鲜少发声表达认同。
每当我回顾那段百年来我国饱受磨难、深陷困境的历史,是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将其扭转乾坤时,即使高呼千遍万遍“毛主席万岁”,亦觉其声犹在耳,绝不过分。然而,我这样的满身旧习,心中杂念纷扰。我总是将这份坚持视为“倔强精神”与“骨气”,引以为傲。然而,须知,劳动人民向共产党所展现的,并非是这种倔强与骨气。
正是由于我对阶级立场理解上的偏差以及对中国共产党认识上的偏误,导致了我在9月18日所犯下的荒谬错误达到了顶点。我那种狂妄自大,无视众多人对于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公开场合与毛主席争论对错,必然会激起众人的强烈愤慨。因此,他人对我进行批评和指责,完全是理所当然之事。
审视我自1953年之前的将近五十年岁月,我自认为投身于革命事业,却最终陷入了改良主义的泥沼;对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言,改良主义又演变成了反动;加之我始终坚持改良主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贯的反动。因此,毛主席曾指责我以笔为武器进行杀戮,当时我在会议上对此颇感不服。待我逐渐领悟其意,方才明白,这句话所指的,是我长期以来的反动言论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
主席再度指责我身为伪君子,我听闻此言,依旧只是轻蔑地一笑,心中并不认同。然而,在深思熟虑之后,我坚信唯有舍弃私欲、怀抱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方能被称为真正纯洁、清白的人。而我,若仍沉溺于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之中,便无法做到纯真无伪,如此一来,便成了伪君子。
主席言道:“我竟能骗人,竟有他人受我蒙蔽,这显然是在指责我这样一个并非完美之辈,竟仍有人对我深信不疑,赋予我好人美誉。这或许正是揭露其真实面目之时。”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自9月18日冒犯了毛泽东之后,梁漱溟真诚地进行了自我剖析,深刻地进行了自我反省,其中毫无矫揉造作之态。
1953年9月,梁漱溟在公共场合对毛泽东提出质疑,自那以后,他便不再有机会单独与毛泽东进行交谈。尽管如此,他依然履行着政协委员的职责,生活待遇并未受到影响,亦未遭受任何组织的处分。
梁漱溟心中依旧怀揣着对毛泽东的深切敬意与浓厚情感。而毛泽东亦对这位同年同月同日生的梁漱溟保持着深厚的关切。
1972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主席的华诞,梁漱溟先生特地将自己的著作《中国——理性之国》献上,以此作为一份独特的生日贺礼。到了1975年9月,在审阅一份文件时,毛泽东主席提到了梁漱溟先生,并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等话语,流露出对梁老先生深切的谅解之情。

三十余年后,当踏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谈及此事时,梁漱溟再度感慨良多,不禁感伤地言道:
当时,我的态度确实不佳,言辞随意,未曾考虑场合,这让他倍感困扰。我更不该伤害他的感情,这实在是我犯下的错误。如今他已离世十年,我心中涌动着无尽的寂寞。
文中透露,梁漱溟虽性格刚烈,实则心怀真情。
2024配资查询网站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